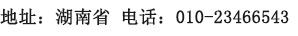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。
生存病毒是一类无完整细胞结构,必须在活细胞内寄生并复制的非细胞型微生物。
虽然病毒是否属于狭义上的“生命体”,如今并没有定论,但它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维持活性。
也就是说,离开宿主细胞,病毒一般也会在几个小时之内失去“生命”。
当然,如果宿主死掉,病毒也会随着宿主的尸体消散。
我们知道,病毒的延续,依靠的不是“质量”,而是“数量”。
追求数量,就需要传播给更多的宿主。
如果追求更多的传播,就需要让宿主的身体出现症状,例如
咳嗽、喷嚏、流汗、恶心、呕吐、腹泻、皮疹、皮肤损伤、出血、坏疽,甚至神经错乱等等。
这些症状,有些会对宿主的身体造成一定的损伤,如果损伤太重,就会杀死宿主。
比如我们上一篇提到的鼠疫杆菌,“黑死病”。
虽然鼠疫是杆菌,不是病毒,但道理是相通的,病毒为什么要把症状弄得这么严重,以至于杀死宿主呢?
如果病毒懂得控制症状,并让宿主尽可能的维持正常的生活及寿命,那么不就大大地提高了传播几率吗?
看到这有人会说,病毒又没有“理性思维”,它如何懂得控制症状,你以为你在玩“瘟疫公司”吗?
共存生物医学非我所长,所以本篇尽量保有对于科学的严谨。
病毒虽然没有“理性思维”,但“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”带来的适应性,要比任何自负聪明的头脑完美得多。
如果控制症状真的可以为病毒带来更大的传播优势及生存优势,那么病毒一定能在进化中学会“适可而止”。
比如“1型疱疹病毒”,感染这种病毒后出现的症状非常微弱,甚至大多数都是无症状的,只是偶尔会引起疼痛的水泡或溃疡,通常称为:疱疹。
这些疱疹通常8-10天就会痊愈,复发的频率因人而异,有可能一个月复发一次,但大部分感染者一年只会发作一次,只有在复发期时传染性最强。
类似的病毒还有很多,这些病毒在与人类长时间的共处下,都表现得很有分寸。
但也没有因此而耽误了传播,疱疹病毒借着疱疹溃破后的体液接触,就悄悄地传染给其他人。
据估计,全球有37亿50岁以下的人(67%)罹患I型单纯疱疹病毒。
相比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(SARS),感染者最初就会出现呼吸困难,发热,全身疼痛无力等症状,一周就会导致宿主休克及死亡,死亡率高达7%。
结果让宿主们重视起来同仇敌忾,从发现到结束,也不过5个月的时间。
所以说,病毒与宿主之间的关系,对病毒进化起着重要的影响。
那些与宿主偏利共生,甚至互利共生的病毒,才能在进化中变得更有优势。
比如HIV(人免疫缺陷),第一例HIV病毒是在美国发现的,至今已流传40多年。
在年,一个国际科研小组在发表研究报告称,随着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感染者日益增多,艾滋病病毒的毒力有减弱的迹象。
原文检索:
RebeccaPayne,MaximilianMuenchhoff,JaclynMann,HannahE.Roberts,PhilippaMatthews,EmilyAdland,AllisonHempenstall,Kuan-HsiangHuang,MarkBrockman,ZabrinaBrumme,MarcSinclair,ToshiyukiMiura,JohnFrater,MyronEssex,RogerShapiro,BruceD.Walker,ThumbiNdung’u,AngelaR.McLean,JonathanM.Carlson,andPhilipJ.R.Goulder.ImpactofHLA-drivenHIVadaptationonvirulenceinpopulationsofhighHIVseroprevalence.
报告称,HIV病毒的潜伏期和携带者的寿命,都平均增长了2.5年。
因为性传播是HIV主要的传播途径之一,潜伏期越长,宿主寿命越长,那么HIV病毒就越容易传播。
与此类似的还有乙肝和丙肝,这些病毒在与宿主相处的时候,都进化得更加温和了。
病毒在进化中,都学会了以退为进,宿主的免疫系统也懂得了减轻免疫反应,你不惹我,我就不惹你,大家各退一步,都有活路。
若不是毒力太强,或者免疫反映过于强烈,宿主与病毒玉石俱焚,那就不会存在能够和病毒平共存的宿主了。
比如天花,天花病毒毒力极强,且传染极快,痊愈后可获终生免疫,因此它们只能被同一个宿主传播一次。
所以天花被它的宿主彻底消灭了,如今,只有少数几家实验室还保存着天花病毒样本。
没办法,既然你不想与宿主和平共存,那么你和宿主,就必须死一个。
原宿主人类是一个非常喜欢“作死”的物种,热衷于探索新鲜、未知的食物。
上文中提到的“SARS”、“HIV”、“天花”,原本的宿主并不是人类。
这些病毒与原宿主,不知经历多长时间的适应,才达到共存的条件。
可人类偏爱探索未知领域,于是遇到了SARS和今年的新型冠状病毒,那只有从头开始,与它们慢慢适应了。
不过,人类作为宿主,并没有与病毒长期适应的耐心,也承担不起死亡的代价。
那些恐怖的新致命病毒,如果往上溯基本上都能找到一个能够和平共处的“原宿主”。
当然,也有例外。
比如“狂犬病”,狂犬病的原宿主是蝙蝠,至今已传播了上千年,却仍然有%的致死率。
就算是埃博拉病毒,在与原宿主蝙蝠共存了0年左右,也接近相安无事了。
如果说埃博拉的致死率在人类身上可以高达90%,是因为它只能达到这么高的致死率。
狂犬病可以让一切可感染的哺乳动物都能达到%的致死率,是因为哺乳动物只有一条命。
狂犬病的高致死率,与他的传播方式有关。
狂犬病的主要传播方式,是由唾液进入伤口,为了避免免疫系统的防御,就会由外周神经侵入到宿主的大脑里。
接着再由脑神经扩散到唾液腺里,当宿主捕食猎物时,再通过撕咬把病毒传播给下一个宿主。
但是,如果宿主只是正常的捕猎,就无法散播病毒了。
如果宿主抓到猎物,就成为了宿主的一顿大餐。
就算猎物跑掉了,因为猎物多是食草类动物,也就不会再去撕咬新的宿主。
所以,狂犬病必须让宿主发疯,去撕咬同级别物种,甚至更高级别的食肉动物。
但如果让宿主神经错乱,就必须诱发脑炎。
可惜的是,大脑对于任何物种都太过重要,如果引发神经错乱级别的脑炎,发疯到去撕咬高级别的物种,必然会致死。
所以病毒能否与宿主共存,和传播方式有很大的关系。
那些通过空气和接触传播的病毒,比如文章开头提到的疱疹病毒、HIV还有最近爆发的“冠状病毒”。
这些病毒依赖于宿主的健康,所以他们要把宿主的症状搞得轻一点,潜伏期长一点,才能够让宿主四处传播。
就算是厉害的病毒,致死率也不会很高,SARS算是很厉害的,WHO公布的致死率也不过7%。
竞争回到我们的问题,那么如果病毒们都毒性低,大家都慢慢复制传播,那不就都能大范围的感染吗?
那为什么还会有病毒要杀死宿主呢?宿主死了,病毒也得死,那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?
因为病毒不止一种,病毒们除了要面对宿主的免疫系统,还需要面对“竞争者”。
如果病毒与其他病毒同时感染宿主,那么那些复制较快,出现症状教重的病毒,就会占据优势。
放在经济学中,我们可以称为:
生产者与生产者竞争,消费者与消费者竞争,生产者和消费者从不竞争。
宿主可以称为“生产者”,那么病毒就可以称之为“消费者”。
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逻辑看下去,那么最近爆发的“致死新冠状病毒”,其实已经不存在了。
这并不意味着冠状病毒不存在了,而是“致死”的冠状病毒不存在了。
我们知道,冠状病毒病毒在最初感染的时候,是因为感染了新的宿主,所以不知道如何和新宿主“共生”。
所以,它会没轻没重地杀死新的宿主。
然后它开始不停的复制,而今天还在传播的,肯定不是第一批毒性最强的病毒。
而是经过3个月筛选出来,更温和的病毒。
如果它还具备强致死性,导致宿主死亡,反而不利于它的传播了。
我们假设此次的“新冠状病毒”在复制进化的过程中出现了3个模型。
第一类,就是第一批感染的病毒,感染后直接致死。
第二类,出现咳嗽、发热,然后被隔离。
第三类,基本没有明显症状,还可以四处走动。
肯定是第三类症状最轻的病毒,传播最广,生存几率也最大。
事实也是如此,如今已经出现了没有症状,但病毒检为测阳性的例子了。
而且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,虽然病毒传播速度没有下降太多,但致死率已经降得很低了(武汉致死率4.1%,全国致死率2.0%),而且还在降低。
从病毒发现至今,不过才三个多月,生物进化的速度,实在令人震惊。
探索就算是人类再进化几千年,面对“未知”的野味,仍然会有剧毒的。
通过本次疫情,也让人类吸取到了教训。
虽然人类文明的扩张,不会因为一次瘟疫而停止。
想要阻止人类文明扩张的脚步,它还不够资格。
但也足够使我们警惕,对待未知的领域要更加的小心翼翼。
最后,愿这片土地的疫情尽快散去,让损失降到最低。
来源:万归藏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